|
刘丹 每一位导演,在创作上都有点个人癖好,比如:是枝裕和独爱夏日的海浪,王家卫钟情迷离暧昧的暖光,理查德·林克莱特则喜欢絮絮叨叨的对谈哲学。 但在贾樟柯这里,总有很多跟流行审美相悖的美学意见。 他看到黄昏的海滩,会觉得很难看,非常讨厌,也无法跟喜欢黄昏沙滩的摄影师合作。 当下演员上镜都追求小脸,但贾樟柯曾为了让人物显得古典,把片中所有人的脸拉长,就像工笔画里的仕女脸一样。奇妙的是,观众并没有发现。 拍《站台》时,贾樟柯甚至希望在所有的光里加一点“绿”,并把围墙都刷成绿色。摄影师问为什么,他答不上来。 《站台》里的绿 色倾向 贾樟柯更喜欢把这些“偏见”称为口音。“每个电影作者的风格和味道转化成语言,就是你的口音。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,你的电影中有没有你的口音?” 因为有很多独特的美学见解,贾樟柯的团队都是相对固定的,特别是在流水的县城故事中,必有铁打的赵涛。 在贾樟柯眼中,县城生活到底美在哪?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废墟、UFO和赵涛? #01 贾樟柯为何沉迷拍县城? 贾樟柯最喜欢做的一种观察,就是县城的进化。 小时候,他母亲的家人都在农村,而父亲家的亲戚都在县城,这导致贾樟柯的暑假是在农村和县城之间反复横跳的。 贾樟柯发现,当商品经济潜入中国基层社会的缝隙,就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。“县城的变化,也包含了我们文化景观的重大改变。”贾樟柯在《电影的口音》一书中谈到。 当中最大的改变,就是一个落后县城突然蓬勃的现代感。 首先是卡拉OK歌厅忽如雨后春笋,几乎每个小镇青年都能哼上一两句港台金曲。在成名作《小武》中,小武的恋人胡梅梅,就是在歌厅里认识的歌女。 胡梅梅很爱唱歌,但也清楚自己一辈子也当不上明星。她最爱唱的歌是王菲的《天空》,彼时,那位歌后的名字还是王靖雯。 腼腆的小武喜欢听,但唱得很蹩脚。这个片段的灵感,是贾樟柯有次在家乡的卡拉OK歌厅唱歌,看到一个非常孤独的男人,他唱得很难听,但不停地唱同一首歌。 贾樟柯刚开始觉得很烦,但后来突然很感动。他觉得这是流行文化给在艰难环境中生存的人,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归宿和可以自我安慰的地方。 流行文化的入侵还发生在书店。 在上世纪80年代初,县城就开始有阅读哲学著作的热潮,在汾阳的书摊就可以买到尼采、弗洛伊德等西方文学和哲学著作,人们见面还会谈“潜意识”。 这种盛况,在今天的书报亭也不太可能重遇。 一位父亲,一脸迷惑地从儿子包里掏出一本《茶花女》。 图/《站台》 1987年的美国电影《霹雳舞》和迪斯科,也在县城风靡一时。贾樟柯第一次赚钱,就是靠跳舞赚的,那时候他还会翻跟斗。 县城变化中的人际关系,也是贾导觉得值得记录的景观。 最开始,《小武》的片名叫《胡梅梅的傍家,金小勇的哥们儿,梁长友的儿子:小武》,后来制片人觉得太长了,就把定语都去掉。 这些细节,都包含着中国县城变迁史。 在经过时代洪流的冲刷后,县城又回归了原本的平静样貌,就像《站台》里那群曾疯狂奔赴未来的有志青年,最终还是成为老婆孩子身边绕、每日沉迷睡午觉的中年人。 很多人会觉得贾式电影无比冗长,节奏慢,戏剧性低,看完就像度过了一个漫长又无所事事的黄昏。 但贾樟柯要表达的正是这一点:大多数活着的人都不过如此,日子重复而平静。 很多人对县城的想象是乏力的,但贾樟柯把这一切看似平静的潜流都收录在镜头里,并形成一种独特的县城美学。 #02 在现实的废墟中,安排一个超现实的UFO 贾樟柯早期的影片,都在无限逼近真实。 在他看来,“真实感”是一个美学层面的概念,比如他不喜欢银幕上常见的漂亮男女,一开口就带着舞台式的腔调。 他更偏好小武那种平凡的外表,因为那就是普通中国人的面孔,还带着一种敏感和自尊。 “起用非职业演员,是我在美学上的兴趣。”贾樟柯说。 演员的非专业性,肯定会带来麻烦,但这位导演有办法,他会在拍摄前约一个月,让非职业演员跟工作人员一起生活,吃饭、打麻将、唱卡拉OK。 他在所有细节上仿佛都有强迫症,上世纪70年代末的戏,绝对不能出现化纤的袜子,不管观众是否会看见;找不到合适的服装,就让赵涛穿他姐姐的旧衣服。 贾樟柯还喜欢录入各种环境中的噪音,比如街道上的人声、汽车声、摩托车声。一些录音师会觉得声音不干净,但他觉得这样最真实。 如果说贾樟柯早期的电影是写实风,那他后期拍的《三峡好人》和《世界》,则呈现了一种魔幻现实。 譬如在一个凉风徐徐的夜晚,对面的烂尾楼突然变成火箭一飞冲天。 又或者在两栋等待拆迁的农民房之间,农民工突然看到一个人在空中走钢丝。 2004年上映的《世界》,更是贾樟柯的魔幻现实代表作。他以一个号称“不出北京,走遍世界”的微缩世界公园,构造了一个豪华的虚拟空间,并把这个乐园里的打工人,称为“飘一代”。 飘一代,最开始是《新周刊》在2000年推出的概念,指当时18岁至35岁的人群,从小城镇去大城市漂泊,是中国的新生代。他们追求自由,无法停止幻想。 而贾樟柯的《世界》,演活了这个词儿。他想表达在城市剧烈发展的过程中,所带来的不真实感和超现实感。 在现实与虚幻之间,贾樟柯还保留了一段独特的废墟美学。 他在废墟中呈现的人和物,都仿佛在进行合理的行为艺术。 当年三峡的拆迁是最让贾樟柯大受震撼的,他到达拆迁现场时,整个城市已经是一个废墟,他当下的第一反应是:是不是外星人来过了? 于是,贾樟柯就在片中安排男女主角,都曾凝望一个UFO。他用电影证明,要真诚地讲述现实,不等于不能用荒诞的超现实手法。 #03 赵涛:一个美学符号 赵涛在贾樟柯的镜头里活过很多种人生。一开始,观众都觉得这是贾导的偏爱,但慢慢发现,如果一个影片中的“含涛量”较低,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 赵涛逐渐蜕变成贾式电影里的一种美学符号: 坚韧、粗粝,有着最平凡也最夺目的女性光辉,在生活的洪流中匍匐前行。 第一次见面时,贾樟柯看到她正在给学生上舞蹈课,批评其中一个学生:“跳舞啊,你得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哑巴,有什么情感情绪,用肢体语言来告诉别人。” 从那时候开始,贾樟柯就十分相信她的理解力和表现力。 《站台》电影里,赵涛独自挑起一段一分多钟的独舞。 赵涛常常在团队中提供一种很独特的女性观察。在拍《三峡好人》时,她一直跟化妆师说“加汗”,因为拍摄的是很闷热的环境,她十分注重体感,要把那种气候演出来。 后来拍《江湖儿女》,赵涛觉得不太了解女主,就开始看大量的庭审记录,以及关于这种女性的报告文学和口述历史,并写人物小传。 她还带领团队组成了一个皮肤工作小组,就是为了逼真还原90年代的皮肤。这种认真的工作劲儿,让贾导很欣赏。 赵涛还是贾樟柯的灵感提供者。在山西省艺校毕业之后,赵涛被分配到深圳的世界之窗,虽然里面有全世界的著名景点,但她每天都被要求跳同一支舞,很快就觉得枯燥和封闭。 这种角落和世界的关系,启发贾樟柯写出了《世界》。 学者戴锦华认为,贾樟柯的电影,是关于生命之河的急缓、汇流、蜿蜒与水中和岸上的偶遇。 贾樟柯对英雄和偶像没有兴趣,只拍他理解的中国人的生活,潜伏在中国的大小县城之中,找到了一个观察农村和城市的有意思的角度。 特别是在贾樟柯镜头下的汾阳,像个谜团一样美。它经过贾樟柯的电影,成为国际观察中国的一扇窗。 此前,作家白睿文一直在分辨贾樟柯最终代表的是中国的口音,还是山西汾阳的口音,最终发现是他的电影的独特口音。 这当中或许会呈现很多独特的“偏见”,但也正是这些不一样的目光,让贾樟柯成为贾樟柯。 参考资料: 《电影的口音:贾樟柯谈贾樟柯》,(美)白睿文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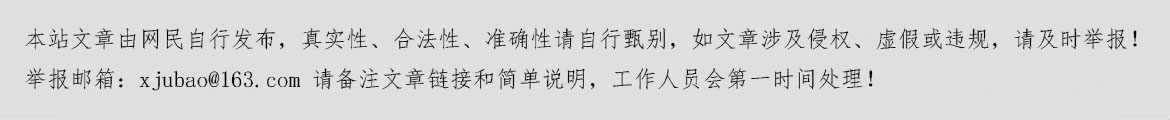
|
|
1
 鲜花 |
1
 握手 |
 雷人 |
 路过 |
 鸡蛋 |

业界动态|博文供求网

2026-01-10

2026-01-10

2026-01-09

2026-01-09

2026-01-09

请发表评论